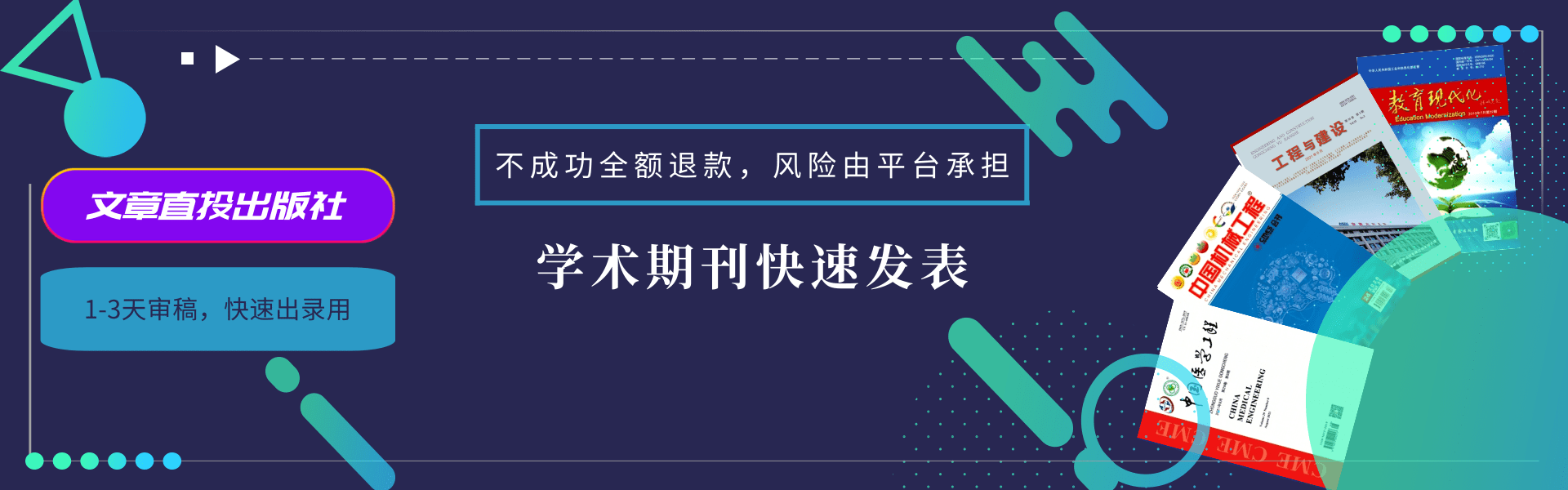本文为陕西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编号:RW-64)成果之一
【摘要】孟子建立其“人性善”学说,运用了孔子“正名主义”的逻辑方法。“人性”乃“人之所以为人者”,一句话,“善”是人性,善才是“人”性。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石,建构了他的伦理学说、“自我”建构学说、政治学说。其“成人”之路径是“顺”着来的,由“四端”而发扬光大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性善论”解放了人的意志,逻辑上剥夺了“自我”作恶的自由;“性善论”不仅激活了“自我”的生命尊严意识,并且会建构起一种“召唤”“期许”的良性回馈机制,从而为“正确”的自我的建构奠定了基石。“性善论”为“仁政”政治学提供了可能,而其乌托邦色彩永远闪现着召唤和激励的理想之光。
【关键词】性善论;正名主义;生命尊严;“自我”的建构;仁政;乌托邦
《孟子·滕文公上》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性善”成了孟子对人性的“命名”。“性善说”无疑是孟子学说的基石,他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说、“大丈夫”说、“仁政”“王道”说等等,都建基于他的“人性善”论之上。孟子的“性善论”甫一提出,就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中心话题之一,被不断地探究、阐释,尊贬吸拒,见仁见智,副墨洛诵汗牛充栋。现代以降,考索的背景与视野又因了欧风东渐及社会剧变,而与“现代性”“全球化”发生了深刻关联,尤其是近年来的讨论。[1]本文试图遵循“理解之同情”原则,从儒家哲学的内在理路,对“性善”说进行逻辑学考察,展显“人性善”之“为何”、“何为”,亦即展显人性善的普遍伦理,究竟如何在每一个个人生命主体中实现“具体化”;展显一种学说真正血色丰盈的“人间性”之所在,以及孟子学说的逻辑体系是如何由此奠基、建构的。
一、“正名”——“性善论”与“人”性——“善”是人性
“正名”本是孔子的首要“施政”纲领与策略。《论语》中说: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正名”的含义是指,“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君’之名之定义之所指,即君之所以为君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君字乃指事实上之君,下君字乃指君之名,君之定义。臣父子均如此例。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义,皆盡其道,则‘天下有道’矣。”[2]孔子自己的“正名主义”的施政理想与实践失败了,但在后世,无论是被作为哲学上的方法论,还是政治学说均影响深远。孟子的“人性”学说是与“正名主义”直接联系的。“正名主义”是孟子建立“性善论”人性学说的首要逻辑方法。
孟子的“人性善”奠定了人之为“人”的基础。
孟子主张人性善,并不是认为,人人生下来便是一位孔圣人,而是承认人的本性中有些因素,本身无所谓善或恶,但如人不加以节制,它就将导致恶。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这是人与野兽共同的地方,它们反映了人身上有动物性的方面。但严格说来,这不是“人性”。“人性”乃“人之所以为人者”,一句话,“善”是人性,善才是“人”性。——孟子截断众流别开生面之根本意义正在这里。孟子明确地从“人禽之别”上来说的,在与告子的辩论中,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
在其著名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论述中,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一段中,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第一反应“恻隐之心”及其纯粹非功利性,巫峡千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下子跳跃到,“无……非人也,无……非人也,无……非人也,无……非人也”,似乎太过“强词夺理”。实质上,孟子滔滔雄辩的内在逻辑是,“善才是人性。善即仁义礼智。无此‘四心’即非‘人’也。”
戴东原说:“性也,人与物各以类区别,成性各殊也。”(《孟子字义疏证》)朱子解《论语·雍也》中“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谓曰:
觚者,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举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则非人,国而不治则不国矣。’”
正是在“正名”的意义上,“人”性善者,即以为“人”性其“所应该”善,即其“所以然”善也。
二、孟子的伦理学
孟子祖述孔子的“仁”的学说,他把孔子思想更加明晰缜密地系统化,如程子所言:“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学说,是典型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其学说体系中,“内圣”又是“外王”之前提。而其“内圣”又以“性善论”、“人皆可以为尧舜”为前提和路径。
儒家的“人”是“人伦”中的人,“入世”的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儒学是“入世”哲学,“入世”是对责任的一份坚持,生命的价值是在“用世”中得以实现和体现的。如后世刘越石所言:“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堂。天下之宝,当于天下共之。”(刘琨《答卢谌书》)
孔孟设计的“成人”路径是“顺”着来的,像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云云,“兴于诗,依于礼,成于乐”云云,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揠苗助长”云云,以及《大学》(依郭沫若先生的考索,“四书五经”中的《大学》“实是孟学”,“它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谓“修齐治平四条目”,分明是由孟子演绎出来的)[3]的“八条目”,更明晰、具体地显示出“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可持续发展”特性。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八条目”实际上只是一条目,就是“修身”。[4]“修身”就是“发扬光大”本性中的善端。如柏拉图言人性中有狮、有多头怪物,亦复有人,教化乃所以培养“人性中之人”。[5]
笔者的《孟子性善论的发生学考察》文中,论析了“爱亲”“敬兄”之心是孟子学说的“生长点”。其整个学说建基于他的“人性善”论之上,而“性善论”的根据就是“仁”“义”,“仁”“义”是其全部学说的核心,同时他把“仁”“义”的最基本的、最开端的意义,落实于人伦之初的“爱亲”“敬兄”之亲情关系。他在奠基“人性善”论时,是把人性作为人内在的根源可能性,具备强大生命力的“生长点”的,从而在本质上是趋向善的。这个“生长点”就是人伦最初的“爱亲”“敬兄”之心,亦即仁、义之“端”。从而展显“人性善”如何可能,亦即展显人性善的普遍伦理,究竟如何在每一个个人生命主体中实现“具体化”;展显一种学说真正血色丰盈的人间性之所在,以及孟子学说的逻辑体系是如何由此奠基、建构的。——这种可以诉诸每一个生命主体“肉身”性的亲切经验,真正地使得“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孔子作为教育家,作为“大成至圣先师”,他开创的儒家学说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教育理论”,因了孟子的“性善”说而画龙点睛,妙笔生花。“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娄章句上》)正是人之为人源初地处于道德践履关系中的人性,作为人内在的根源可能性,犹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始于足下,“成人”的路径依赖,与时俱进地“习与性成”,康庄广衢,水到渠成了。
三、“性善论”与“自我”的建构
“性善论”解放了人的意志,使其有了从善的而不是作恶的自由:作为一种召唤,一种期许,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尊严意识,激发人的善意或爱心,人心便发出了对至高无上、永恒神圣高贵的善的神往和爱慕,使人心中充满了爱,一往情深,用善的愿望取代了恶的欲念。
“性善論”逻辑上剥夺了“自我”作恶的“自由”。
古今中外主张“人性恶”者,无非是以人皆有之的与生俱来的欲望存在为依据。孟子不会看不到欲望问题,他也承认无节制的欲望的泛滥导致了恶,因此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但如前所论,孟子以“正名主义”论证了“动物性”非“人性”。进一步,孟子极其深刻清醒目光如炬地始终保持了对欲望这个概念的“活泼泼”的现实感。正因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驱使着人的沉沦,这是源初意义上的一种“不由自主”的“作恶”不自由状态,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章句下》);更深刻地,孟子看到,现实的愿望存在状态,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章句上》)——一个人的欲望是复杂的多样化的,加之不同欲望扞格制衡,也就使得具体个人的任何现实的欲望都不可能全无节制。而且,如所谓“浮士德精神”揭橥的人之永不满足亦是易于厌倦的特质,构成了对任何一种单一的欲望的自我约制。更不必说,在具体的人群网络中的任何个体,是无往不处于“规训与惩罚”的强力制约中。
正因为人是“人伦”中的人,“性善论”不仅激活了生命“自我”的生命尊严意识,并且进一步会建构起一种“召唤”“期许”的良性回馈机制。因为“证明”不可能是绝对的自我证明,“承认”也不可能是绝对地自我承认。我的名字我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钱锺书先生曾说:“凡可以成我相、起我执、生我障者,虽离外物,不与生来,莫非‘我’也,‘性’也。……苟疾苦而不至危殆,贫乏而未及冻馁,险急而尚非朝不虑夕,乃至出息不保还息,则所‘全’之‘性’、所‘为’之‘我’,必超溢形骸身体,而‘名’其首务也。‘名’非必令闻广誉,口碑笔钺也,即‘人将谓我何’而已。塞天破而震耳聋之大名无不以‘人谓我何’托始,如雄风起于萍末焉。名属我相;我相排他,而名又依他,以人之毁誉,成己之声称,我慢有待乎人言。爱身惜生之外而复好‘名’,此人之大异乎禽兽者也。古人倡‘名教’,正以‘名’为‘教’,知人之好名仅亚于爱身命,因势而善诱利导,俾就范供使令。刘熙载《昨非集》卷二《书<列子·杨朱>篇后》:‘名与善相维者也,去名是去善也。……名不足以尽善,而足以策善,杨朱则用以抑名者抑善也。’”[6]——依此而论,“我为谁”即人“人谓我何”;人谓我何,又赖“我愿”人“谓我何”;“我愿”则含蕴了前述的“召唤”、“期许”的回馈机制。
逻辑言之,“自我”经历经验而建构,而经验只能是血肉之躯的人的“经验”。“自我”是什么呢?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不仅是一个身体外加一个大脑:我们是住在我们身体里面、控制我们身体的“那个人”。就西方哲学史话语论之,或同之于柏拉图的灵魂概念,然笛卡尔《方法论》中之“我”本质上乃一思维实体,休谟《人性论》中之“我”是一种心灵知觉。但更重要也更亲切更迫切的是,人的“自我”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能够建构“自我”,是在生命活动中力图塑造“自我”——从而实现期许的真正的善,而这个“善”则是一个“先在”的价值观念,意即“我”一来到世间立刻迎面遇上的儒家话语,建基于“人性善”论之上的价值体系——不必说后来的两部蒙学教材《三字经》《弟子规》开篇即谓“人之初性本善”“弟子规圣人训”云云。自我意识就是将自身与一定欲望相统一从而产生了行为的动机。所以,自我是关于个人存在的感受,是个人藉此向世界言说的独特方式,是个人欲望的一种结构。自我的塑造是在自我和社会文化的“合力”中完成的,可化约为:自我期许与自我约束之机制,即个人意志权力——在《孟子性善论的发生学考察》文中,把这论述为“英雄崇拜”意识;他者力量,即社会规约、精英思想、家庭国家权力。自我意识的塑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本质塑形、改革和变革。
另一层面,人对自己的深层了解,只有穿越他人的反射与反照,通过别人而为我所知。据说,现代科学研究认为,人是唯一能接受环境暗示的动物。以普遍的经验观之,积极的暗示,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产生良好的影响,激发人的内在潜能,发挥人的超常水平,使人进取,催人奋进。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招招舟子,人涉骯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豫让曰:‘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汉书·贾谊传》谊上疏陈政事,亦引豫让此数语而申之曰:“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矣”。
同时,“我”的世界又是通过“以己度人”建构,以君子之心度人则人皆君子,以小人之心度人则人皆小人。云萍偶遇,针芥易亲,近思以远取,鉴往而知来,自本身之经验着眼,于切己之情景会心,即旷代亦相知,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于是更进一步,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召唤机制,出幽迁乔,“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矣”,即“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离娄章句下》)西哲普罗泰戈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在孟子那里,这个“人”应指圣人。“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离娄章句上》)——朱子注曰:“法尧舜以尽君臣之道,犹用规矩以尽方圆之极,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称尧舜也。”
四、“不忍人之政”——孟子的政治学
1、孔门提倡“德教”与“德政”,孟子的“仁政”“王道”
孔孟儒学中,个人修养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孟子哲学的方法论,根本上是以历史为依据的经验主义,正名主义亦统摄于其下。在他的言说中,尧、舜等圣人作为“人伦之至”是理所当然而不证自明的,所以然者,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朱子注曰:“性者,得全于天,无所污坏,不假修为,圣之至也。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尽心章句下》)。孔子亦有言:“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摩罗先生在《国王的责任与权力》一文中讲到,远古时代,国王的权威是确确实实建立在为老百姓谋求福祉和利益的基础上。生民最基本的要求是老天爷风调雨顺,以确保五谷丰收、六畜兴旺。能够祈风降雨的巫师在这样的社会不但是知识权威,而且是通天统地的神灵和为民造福的道德英雄,他们因为承担着、而且忠实地履行着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职责,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王者。那时的国王是当时人类文化(比如巫术文化)最高水平的代表人物,这种“君师合一”现象在中国一直持续到了周代,像孔孟津津乐道的偶像周文王,就是巫术文化集大成者,八卦文化的代表人物,当然更是“仁君”之翘楚、“王道”之师表。[7]
孟子的政治学说,突出点在于论证了实现古圣王之治即“仁政”——亦即“王道”的简易性与可操作性。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章句上》)“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这样,建基于其“人性善”论之上人性论、伦理学、政治哲学,从源初一点“不忍人之心”发扬光大,养雏成大鹤,种子作高松,由内圣而外王,“金声玉振”而“集大成”。
2、得民心者得天下——政治合理性依据
另一层面,孟子的“性善论”提供了中国传统中最深刻的政治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善推其所为”,是得民心的关键,“得民心者得天下”。反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尽心下》)追根溯源归根结蒂,这原来就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证明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胞物与“民为邦本”,建构了一种有两千年传统的精英政治运作模式,就是培育与铨选才德之士以牧民,并以道德激励、物质奖惩和监察举报等等举措与机制,维持整体国家治理,以谋求全民福祉为基本导向,“保民而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而“王道”之起根发苗,正由于一点“不忍人之心”之发扬光大。(《梁惠王章句下》)
3、乌托邦色彩
孟子由“人性善”推演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乌托邦愿景,体现出登峰造极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乐观光明的强烈色彩。如孟子引孔子之叹“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真有“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之感,千载之下悠悠众口知我罪我均缘于此。那么,乌托邦究竟何为?
按当代美国哲学家蒂利希的说法,“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8]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尽心章句上》)
理想主义只有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如蒂利希所阐释的,乌托邦由于体现了人在“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或者说“应该是”的那种东西,所以它是对人的存在本质的证明和肯定。人作为一种自为的存在,标志着“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这种可能性标示出人的主体性对现实境遇的超越前景,在超越有限性的期待中,决然走向乌托邦之途,乌托邦的生命哲学意义就在于,使人们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上,在生命中唤起理想的激情。
同时,正如孟子所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亦有沉沦的趋向,这就必须依靠乌托邦理想为人性鼓起飞升的风帆。毕竟,人是靠希望活着的,没有了希望,所谓的人,除了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之外,就什么也不是了。正如鲁迅说的:“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所以,“人性善”之理想国的永恒追求,黄金世界的永恒憧憬,“超凡入圣”的永恒期慕,从根本上保证了人之为“人”的存在,保证了这个世界是一个真正的属“人”的世界。
【注 释】
[1] 刘澍声.孟子性善论发生学考察[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1.4(1)86.
[3]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729.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215.
[5][6] 钱锺书.管锥编(2)[m].北京:中华书局,1986.6(2)1163.519-520.
[7] 摩罗.国王的责任与权力[j].读书,2007.10.
[8] 蒂利希.乌托邦的政治意义.蒂利希选集(上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9.137、135.
【作者简介】 刘澍声(1964-)男,陕西洋县人,文学硕士,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中文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