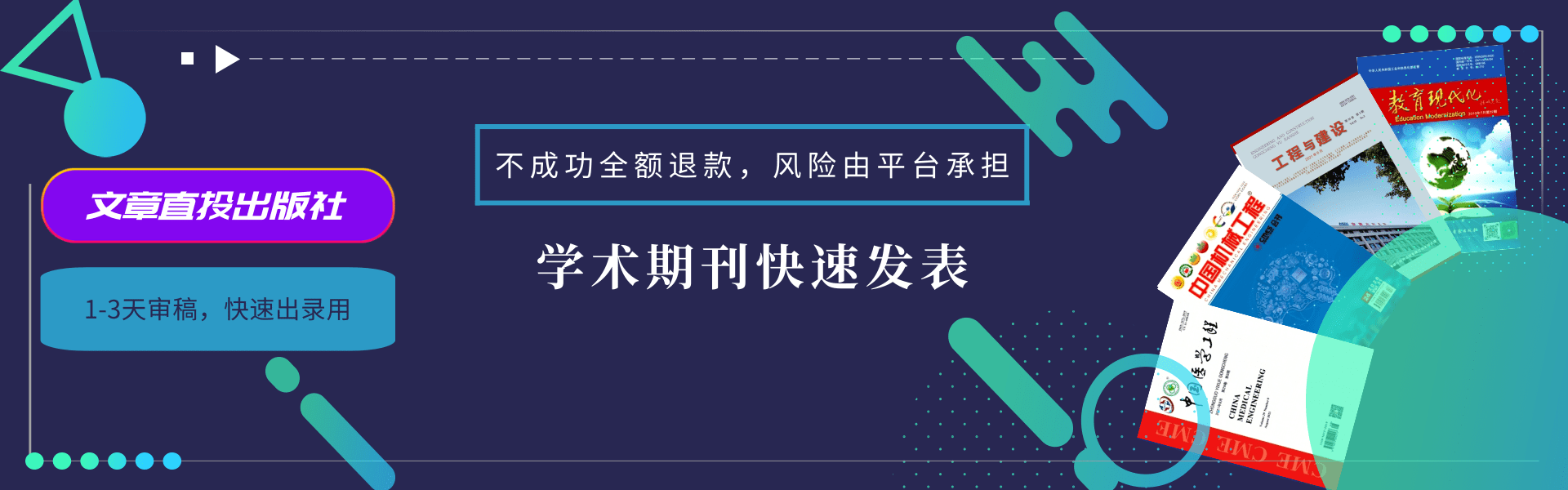彭 飞
摘 要: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以四十年代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为主线,描述她与几个不同类型男性的情爱纠葛,讲述她从一个满怀希冀的少女到命丧黄泉的老妇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一个在命运面前有所抉择的女人的进取、接受、无助。个体性故事的讲述中,渗透的是普遍的人生感受,折射出王安忆深邃的爱情理念。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长恨歌》 王琦瑶 错位 爱情 人本哲学
从故事情节来看,《长恨歌》分成了三部:一是写王琦瑶从一个提着花布书包的女学生,到偶然的进片场、开麦拉、拍照片,逐渐成了“沪上淑媛”,成了“三小姐”,成了国民党某政界要人的金丝鸟,而后随着李主任猝然消逝成了乱世中苍凉的一景。二是写邬桥避难后,王琦瑶携带着西班牙风格的木匣子回到了平安里,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结识了只能爱不能相守的遗少康明逊,并生下了女儿薇薇。三是写薇薇渐渐长大,王琦瑶与薇薇的朋友张永红相处融洽,对时尚有着一致的领悟与感受力。薇薇出嫁了,远走美国,年老、寂寞的王琦瑶将希望寄托在复古派“老克腊”身上,在阴差阳错中被张永红的男友长脚所劫杀。
整篇小说讲述的似乎是一个陈旧的海派故事,只是王琦瑶的个体人生经历,但是这位“上海弄堂的女儿”,却是浓缩了的上海精华,是某类女性的群体意象,是人类长河中女性的悲剧缩影。黄若然曾说:“王琦瑶的人生中,慢慢被磨灭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作为人的独立精神,这不仅是那个时代里按部就班地过着上海生活、想着上海往事的上海人心中曾有过的想法,也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共有的人生价值。王琦瑶不是个体,而是一个代表着群体的意象。”[1]从小说第一部第一章来看,上海的弄堂千人一面,上海的闺阁一幕接一幕,上海的鸽群见证着一切悲喜,冗长的飘忽的文字是想告诉我们:王琦瑶是一个典型,是上海弄堂女儿的化身,是无数渴望幸福的女性的缩影。正如小说所写:“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2]王琦瑶在小说开篇便以群体形象出现,她命运的起落浮沉,她与男性的情与爱,传递了女性作家对爱情的独特领悟与感受。
一
爱情是存在的。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和程先生之间有着一段浪漫的爱情。经片场导演的推荐,王琦瑶去程先生的照相馆拍照片,两人从相遇到相识。二十六岁的程先生,在拍照过程中感受到了王琦瑶的美,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真是月朦胧鸟朦胧。”他在暗房里急切地洗着王琦瑶的照片,仿佛她向他走来,竟感到一丝心痛。程先生对王琦瑶的一见钟情,在心底的深深喜欢,这正是爱情悄然而至呀!程先生约王琦瑶去看电影,中间坐了个蒋丽莉,那种暧昧,那种悸动,是多么美好!程先生爱着王琦瑶,鼓励她竞选“上海小姐”,而蒋丽莉爱着程先生,所以也热烈附议。于是,这场爱情慢慢地变成了三角恋。王琦瑶明知程先生的心全在她身上,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尽力撮合蒋丽莉和程先生。一个偶然,蒋丽莉看到了程先生给王琦瑶拍的照片以及后面的题词,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一厢情愿。
程先生对王琦瑶的爱是纯美的,单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所谓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互相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性爱、理想和责任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3]起初,对于程先生的邀请,王琦瑶为和蒋丽莉达成一种社交上的平衡,不是出于好感、爱慕。程先生成了王琦瑶的护花使者,始终追随,奉陪到底,如“王琦瑶即便是个影子,他也要追随的;这个影子被风吹散,他也要到那个散处去寻觅”。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单相思,一种柏拉图式的恋爱。然而,随着时间的脚步,两人的心越来越靠近了,演化成了真正的爱情。他们得心应手地拍着照,天南海北地谈着话,一个说,一个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个两心相印的时刻,这种时刻,没有功利的目的,往往一事无成。在繁忙的人世里,这似是有些奢侈,是一生辛劳奔波的一点闲情,会贻误我们的事业,可它却终身难忘也难得”。[4]从作者的叙述来看,爱情是美好的,爱情是宝贵的,爱情是难忘的。虽然王琦瑶的爱不够热烈,但也有这一分两分的同心啊!
随着王琦瑶入住爱丽丝公寓,程先生多次询问无果,竟去苏州寻找所爱之人的踪影。一切都是那么茫然,一颗心为爱火灼伤着,心如死灰。十二年后,王琦瑶怀了一个不能说出父亲名字的孩子,与程先生偶遇在淮海中路的旧货行。程先生依然孑然一身,主动照顾她的生活,而此时的她才明白失去了爱的资格,惟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而等了王琦瑶大半辈子的程先生,在小孩满月后,却无法跨过近在咫尺的一步,断绝了来往。
王琦瑶与程先生的这段爱情,宛如杏花春雨一般,淅淅沥沥,却又刻骨铭心。程先生曾多么痴情地爱着王琦瑶,而她却如此轻描淡写。一切都已沧海桑田后,程先生再次出现在王琦瑶面前,而他却感觉咫尺天涯,最后索性不进则退!
二
爱情是渺小的。
程先生与王琦瑶不紧不慢谈着恋爱,而王琦瑶凭借“上海三小姐”的名气,参与了百货公司的剪彩,结识了李主任,匆匆地搬进了爱丽丝公寓。“王琦瑶也不是爱他,李主任本不是接受人的爱,他接受人的命运……她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力,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王琦瑶的心想着往高处飞,“在良娼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
按照马斯洛的人本哲学来看,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前三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就是对生存的需求。”[5]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横在了头顶……窗框的木头也是发黑的,阳台的黑铁栏杆确实生了黄锈。”而爱丽丝公寓,是流苏和绫罗织成的世界,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住的、吃的、用的,都是无比的精致与温软。李主任的身份显要,给了王琦瑶足够的踏实感,“有了李主任就有了一切似的”。为了生存的需求、安全需要,王琦瑶毫不犹豫地舍弃了程先生的爱。
重返上海后,王琦瑶回到了平安里,在护士教习所学会了注射,过着自食其力的日子。白天匆匆忙忙的,夜深人静时只能独自数着时间一分一秒。二十五岁的她,认识了严家师母,从而也认识了毛家舅舅,开始另一场秘密的恋爱。在康明逊与王琦瑶调情的言语中,她始终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好在一切都成空后,将那可怜的爱变成了劫后余生。康明逊是家里的唯一男孩,但是二房所生,也是在犄角里求生存,与王琦瑶有点同病相怜。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除了眼前的快乐,他是不可能娶王琦瑶的。他们是纯粹的爱情吗?“他们本是以利益为重的人生,却因为这段感情与利益向背,而有机会偷闲,温习了爱的功课。”[6]如果他们之间有所谓的爱,性欲的成分也远远大于爱欲,彼此之间的关系仍停留在马斯洛人本哲学所说的第一个层次,注重自己的物质利益、性欲需求。因而,他们的爱不会由薇薇的出生而有圆满的结局,最终会随着性的消逝而断绝。
三
爱情是错位的。
郑庆民在《北方文学》中说:“他们并不能承载美丽优雅的上海女子的幸福与梦想。所托非人,又无人可托,王安忆写的,不仅是上海女子的悲哀与困境。”[7]王琦瑶是一个很有主见、有追求的上海女儿,在一次次错位的爱情中,她将自己的幸福托付于男性,最后落得个惨死的结局。
王琦瑶的爱情是从未心心相印的。程先生深爱着她,她却漫不经心,只是将他看做了一个“垫底”。在身份显赫的李主任出现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其怀抱,而将程先生忘得烟消云散。王琦瑶与李主任之间,更是错位的,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他,除了漫无天日的等待之外,只收获了一小盒金条,而这最后竟成了灾难的始作俑者。康明逊是一个懦弱的男人,“王琦瑶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为他做什么都肯”以至于生了薇薇,独自将其抚养长大。身份与地位皆不错的程先生爱着她,而她却要拣更高的枝头。生活重新回到了平地,她爱上了康明逊,而康明逊只把她当成了怀旧时的慰藉。王琦瑶有意识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但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巨手将一切颠倒。正如陈瘦竹所说:“人们持续地觉察到人类命运总是被不受控制的因素所支配……那么人生悲剧便存在于这持续的觉察之中。”[8]美人迟暮之时,她认识了二十六岁的“老克腊”,开始了一段忘年畸恋。为了挽留住“老克腊”的爱,她真心实意地拿出了雕花木盒,“想叫他陪陪她,陪也不会陪多久;倘若一直没有他倒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了。”李主任闯进了她的生活,点燃了她的繁华梦,留给了她一个尴尬的开端。“老克腊”进入了她的生活,煽起了她对幸福的渴望,她的孤注一掷加速了这段感情的结束。爱她的人,她不爱,不爱他的人,她却爱得痛彻心扉。生活是这般残酷,爱情是如此滑稽。
王琦瑶的悲剧令人警醒。她总是试图从男性世界里去攫取幸福,而这些男性压根都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苍凉过客。或许,爱情是美好的,众生皆趋之若鹜。其实,爱情只是生活的点缀,而不是生活的全部。与其将希望寄托于男性,不如从物质到精神上彻彻底底地独立,真正的爱情或许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也才能从生存的层次跳跃到爱与归属的层次。
注释:
[1]黄若然:《<长恨歌>中王琦瑶人物形象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4][6]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0页,第64页,第180页。
[3]马克思 http://www.baidu.com/
[5]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7]郑庆民:《男性世界女性化的悲剧——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北方文学,2012年,11月刊,第16-17页。
[8]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和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彭飞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4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