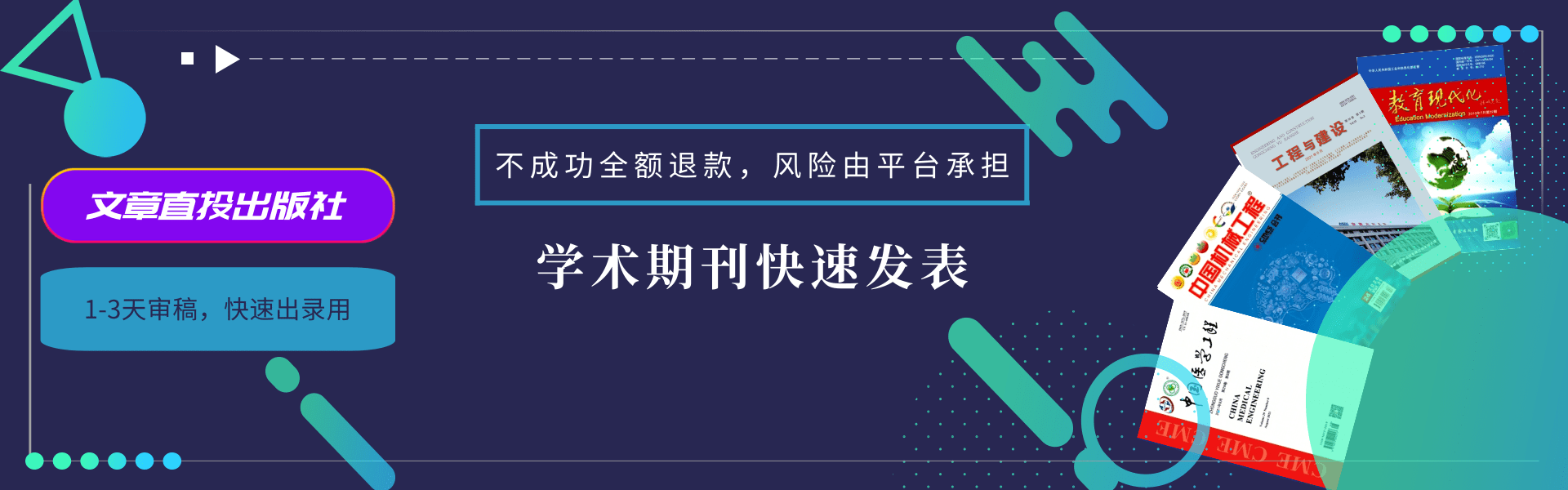摘 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戏剧相对繁荣,英国戏剧界涌现出一批颇具特色的剧作家,戏剧又一次成为英国文学的主要形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剧作家们试图努力颠覆传统,展示人类生存问题, 其剧作的语言特色更是耐人寻味。 英国五十年代的戏剧大都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色彩,反映人的生存状况或社会现实,同时这一时期的作品对英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 英国戏剧 主要特征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度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4BWW007)和2014年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2014lslktziwx-19)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50年代是英国戏剧文学的一次高潮,也是20世纪英国戏剧文学的第二次高潮,对当代英国戏剧乃至整个世界戏剧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在人心中留下了难以平复的阴影,人们对世界开始产生怀疑,绝望。一些英国戏剧家在继承现代主义作家的叛逆精神的同时又试图努力颠覆传统,展示人类生存问题,其戏剧手法别致新颖,将戏剧推向新的进程。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英国的戏剧的舞台上撕下了“荒诞派戏剧的种子”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则拉开了这一时期戏剧创作高潮,许多剧作家开始审视二战后英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述他们对英国社会历史的关注,如哈罗德·品特、威斯克、爱德华·邦德、约翰·阿登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戏剧作品向人们展示战后历史,研究社会道德、文化,揭示战后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
本文将对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戏剧的主要特征进行研究,从这一时期的主题特征,语言特色以及这一时期剧作中反映的社会性和政治色彩进行分析,探讨这一时期的戏剧对当代英国戏剧的影响乃至世界的影响。
一、1950年代英国戏剧的主题特征。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戏剧大都被冠上荒诞派戏剧的标签。剧作家通常通过戏剧的主题来体现对现存世界的不满。法国荒诞派剧作家欧仁·尤内斯库对“荒诞”这个词做了解释说:荒诞指的是丧失了目标,被割断了宗教,抽象的和超自然的根基,人垮了,人的所有行为都变得没有意义,毫无用处,不协调。”[1]这一简短语言高度概括了荒诞派戏剧的主要特点。人类对生存环境和宗教信仰的质疑,整个世界似乎毫无意义,荒诞至极。荒诞派剧作家对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质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质疑,以及对现存世界的质疑,这一主题特征贯穿于荒诞派的始终。
英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有塞缪尔·贝克特、约翰·奥斯本特、哈罗德·品特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奠定了英国荒诞派戏剧的基础,影响颇深。《等待戈多》是一出两幕剧,文中以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佛拉季米尔的对话为主线,向观众展现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世界。就《等待戈多》情节而言,它打破了传统戏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的束缚,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名为戈多的神秘人物,至于戈多是谁,他什么时候来,他们却一无所知。空荡荡的舞台上唯有一颗孤零零的树预示着,在战争的摧残和破坏之后,世界陷入一片荒芜,单调乏味的状态,人在这个荒芜的世界不断迷失,怀疑存在的意义。
在《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的对话象征着这个世界生活是如何单调,枯燥。它强调着通过各种反复发生的情景而变得具体化的存在主题和一个空荡荡的世界。如在第一幕结尾处,爱斯特拉岗问道:“恩,咱们走不走?”佛拉季米尔回答说:“好,咱们走吧。”[2]但是他们仍坐在那里,谁也没有动。在第2幕的结尾,戈多仍然没有出现,两个流浪汉站在那棵树下说着同样的话,只不过是互换了下台词罢了。贝克特的另一部荒诞剧《结局》着意描写的也是人类在一个荒诞无稽的世界上的尴尬处境。世界就像一座监狱,个体在这个监狱里服从最终的放逐。被指定给人的地位在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
哈罗德·品特也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深受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戏剧创作理念和风格的影响,品特根据个人的生活体验及他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创作了一部部独特风格的“威胁戏剧”。在他的作品《送菜升降机》中剧中的两个人物班和格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展开了一段段毫无逻辑的、零碎不合理的对话,向观众展现其生活的无意义性和命运的不可知性。透过荒诞不经、神秘离奇的戏剧情节,展现了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世界的荒诞性。这和《等待戈多》中爱斯特拉冈和佛拉季米尔的谈话情节异曲同工,都是通过荒诞的闲聊,在等待神秘的未知过程中体现存在的主题。它们都缺乏连贯的故事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都试图以荒诞不羁的形式表现人在荒诞世界里的生存状态。品特的另一部剧作《生日晚会》中的对白模式也充满着弦外之音,该剧和《等待戈多》一样,都是对人类存在现实的思考。
欧仁·尤奈斯库在他的《解毒剂》中说:“我们的戏剧是一种对人的命运整体提出疑问,对我们的存在状况提出疑问的戏剧。”[3] 荒诞派剧作家通过对人类生存在一个毫无超验性的世界里的无意义的探究,对生存现状的质疑,展现了生存这一主题的特征,他们不是以或多或少的抽象的和理论的方式揭露荒诞,而是为荒诞提供一副物理又文学的画像。在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里,生命的存在就像是一场毫无意义不可终止的“牌局”。
二、1950年代英国戏剧的语言特征。
马丁·埃斯林在其《荒诞派戏剧》中说:“荒诞派戏剧倾向于彻底地贬低语言,倾向于以舞台本身的具体和客观化的形象创造一种诗。语言本身在这一概念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优于人物说出的词语,有时甚至与其矛盾。”[4]语言是人类之间的交流工具,作者通过语言向读者或者观众传递信息和思想,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剧作家来说,他们对语言的作用产生了质疑,并意识到语言不能给人一种真正的交流,语言在表达思想和存在者之间显得苍白无力。剧作家往往以“反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荒诞。在舞台效果上也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停顿,如在《等待戈多》中大部分对白缺乏逻辑推理,没有连贯性,词不达意,不知所云。如《等待戈多》第二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佛:等一下……我们拥抱……我们很高兴……高兴……既然我们很高兴了那么我们干什么……我们等待……瞧瞧……想起来了……我们等待……既然我们很高兴……我们就等待……瞧瞧……啊!树!
爱:树?
佛:你不记得了!
爱:我累了。
佛:瞧着它。
爱:我什么都没看到。[2]
这段对白毫无逻辑可言,前后矛盾,完全失去了语言作为交流的能力,对话内容也较空洞,思维混乱,存在大量的重复,停顿,沉默。贝克特拒绝语言。正是语言的这种纯粹的声音,正确诠释了一个已经失去意义的世界,在毫无意义的对话,停顿,沉默中,一切变成了无意义的“棋局”。
在品特戏剧作品中也频繁出现删节号和沉默。在台词中出现模棱两可的不确定语言,使得读者和观众始终无法猜测其真正意图。语言的含混不清、破碎、答非所问也是其特点之一。剧本《看房者》中有这样一段话,当阿斯顿问到流浪汉戴维斯的出生地和经历时,以往谈吐自如的他立马变得磕磕巴巴起来:
阿斯顿:你是威尔士人!(停顿)
戴维斯:呃,我到处,你知道……我意思是……我四处……
阿斯顿:你生在什么地方?
戴维斯:(阴沉的)你是什么意思?
阿斯顿:你生在什么 地方?
戴维斯:我……呃……这有点难,就像,回忆过去……明白我的意思……回到过去……很久以前……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就像……你知道……[5]
哈罗德·品特的戏剧有着“威胁戏剧”之称,这是因为在其戏剧作品中充满着神秘的威胁感,笼罩着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超自认气氛,人物之间的对白也充满着权利的角逐。从《房间》、《归家》、《生日晚会》、《升降机》、《看房者》所有这些作品无不带有“威胁”的特点。在《生日晚会》里,品特展示了他能够何等的有利于压迫和控制:在一次使人联想到盖世太保的方法的审讯中,斯坦利遭受了某种压力,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认不出自己的形象了”。这一暴力强调了词语令人无法忍受的权利。这种暴力从此侵入了所有领域。
语言在这一时期已经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了,它的分裂和意义的消失导致了一个诗的世界的 ,一个无意义的文化在一个荒诞的世界的诗性表达。通过戏剧家笔下的人物,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在说话。
三、1950年代英国戏剧中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国力大大削弱,受二战的摧残,英国人民在精神和信仰方面临着严重危机。而传统戏剧中那种“矫揉造作,缺乏真实感的舞台表现手法:奢华的场面,过分的感情表露,诗体的台词和不自然的动作”[6]被剧作家们认为传统的戏剧无法准确反映人的生存现状和现实,他们试图打破传统戏剧的束缚,用新的戏剧模式来表达二战带给人们的伤痛及心理阴影。科林·钱伯说:“战后英国戏剧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社会的框架内开拓了一个政治的天地,一个公众的而不是个人性的戏剧视角。他们关注的是社会,关注的是那些与社会政治共鸣的个人命运。”[7]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戏剧创作大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政治色彩。
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的主人公吉米,来自社会下层,受过高等教育,却只能无聊地经营一家糖果店,对中产阶级所代表的一切恨之入骨。他所采用的语言和动作是对中产阶级的保守和温情的反叛,他在思想上有着淳朴的左倾意识。吉米的愤世嫉俗,继续发泄但又无力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现实,反映了战后这个“福利国家”大部分人的情绪,这部分人主要来自社会底层,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仍被排除于中产阶级之外。剧终时吉米和艾莉森玩的松树和狗熊的游戏,这是儿童或不成熟的恋人之间经常玩的游戏。这与当代一些青年一样,他们在心理上拒绝长大,不敢面对现实和社会压力,这或许是他们躲避痛苦现实的一种方式。因此这部剧带有明显的社会意义,现实生活中的观众或许能从吉米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缩影。
战后一些其他的剧作家,如威斯克,约翰·阿登等创作的戏剧都带有很明显的社会和政治色彩。他们坚信,戏剧应该为社会服务,表达底层劳动者的心声。威斯克的三部曲《掺麦粒的鸡汤》、《根》和《我在谈论耶路撒冷》都反映了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和理想破灭的主题。《掺麦粒的鸡汤》中的萨拉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及热情表达了威斯克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也代表着他的政治热情。在整个剧中,萨拉不时提着水壶这一形象向人们展现了她在剧中的意义:她在给他人的精神提供乳汁,她是他们的精神母亲,是剧作家理想国的灵魂。但他们实际上都明白,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摇摇无期。而《我在谈论耶路撒冷》中萨拉的女婿和女儿从伦敦搬到乡下,试图在那里继续经营他们社会主义的残梦,但无奈在资本主义的威逼下,也不得不放弃理想的碎片。这也反映到现实生活中来,尽管在那个年代资本主义遭到人们质疑,但是社会主义的火苗仍然抗不过资本主义的威逼利诱。
同一时期的剧作家约翰·阿登的戏剧在创作风格上大胆创新同,虽然与奥斯本和威斯克在创作中有很大差异,但其剧作是政治思想和个人灵感的结合,带有问题剧的特点。他的成名作《木思格雷夫上士的舞蹈》中一名英国士兵的妻子被当地恐怖主义分子杀害,此后,一些失控的士兵便借夜色大肆杀戮当地的妇女和儿童。主人公木思格雷夫上士是一个极端危险的理性疯子,但他又是一个虽败犹荣的人物。这部反映社会真实的剧作就是要观众意识到木思格雷夫身上的可怕的暴力逻辑,因为这种逻辑还在以不同的形式在现实中每天重复着。人们痛恨他身上的暴力,但却敬佩他的信仰。木思格雷夫上士身上所表现出的为了社会的秩序,规范而大开杀戒的逻辑,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暴力的借口。虽然阿登的这部成名剧在表现道德意义时不愿明确自己的观点,但剧中主人公却又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载体,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政治色彩。
当然贝克特、品特的作品中也有他们的社会性和政治色彩,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就是在那个荒诞的世界里,人们对生存意义的质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排斥,利用毫无逻辑感的对白去揭发那个时期深层的社会本质。从奥斯本,威斯克,阿登的剧作中,看到社会问题日益成为剧作家创作的一种重要体裁,在探讨人类生存的问题中越掘越深,掀起了英国戏剧的又一次浪潮。总之20世纪50年代后的剧作家们不仅富有创新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色彩。
四、结语
纵观20世纪50年的英国戏剧,从其创作的主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二战的破坏性和残酷性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从其语言的特征中反映在这样一个受破坏的世界里,人们的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语言在表达这种创伤时已经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正是在这种主题和破碎语言中我们中展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多多少少带有政治色彩的笔调,其对英国当代戏剧乃至世界戏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后来的汤姆·斯托帕德、大卫·埃德加、大卫·海尔抑或是女性戏剧作家卡里尔·丘吉尔,都受到五十年代这批剧作家的影响,在寻求自己独特的创造风格中创造出更好的剧作。综观50年代以来的英国戏剧,就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戏剧已打破了传统戏剧体裁的束缚,政在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英国戏剧的舞台上,已经再也看不到由一种流派或一种体裁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了。[6]
英国20世纪50年代的剧作家反对传统,怀疑真理,人类存在的意义,试图从简洁的剧作情节中勾勒人的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质疑。他们打破了传统戏剧的表现方式,使戏剧走向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他们利用自己的剧作把社会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来表达对当代社会的不满和愤怒,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关注社会问题,使英国戏剧再次繁荣。
参考文献
[1] 王佐良,周钰良.英国20世纪文学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432.
[2] 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M].余中先,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85、101.
[3] 转引米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歇尔·吕普吶.荒诞派戏剧[M].陆元昶,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08.
[4] 艾斯林.荒诞派戏剧[M].华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9,10.
[6] 王佐良,周钰良.英国20世纪文学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443,431.
[7] 何其莘.英国戏剧史[M].译林出版社,1999:300.
[8] Colin Chambers and Mike Prior, Playwrights Progress Patterns of Postwar British Drama, Oxford: Amber Lane Press, 198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