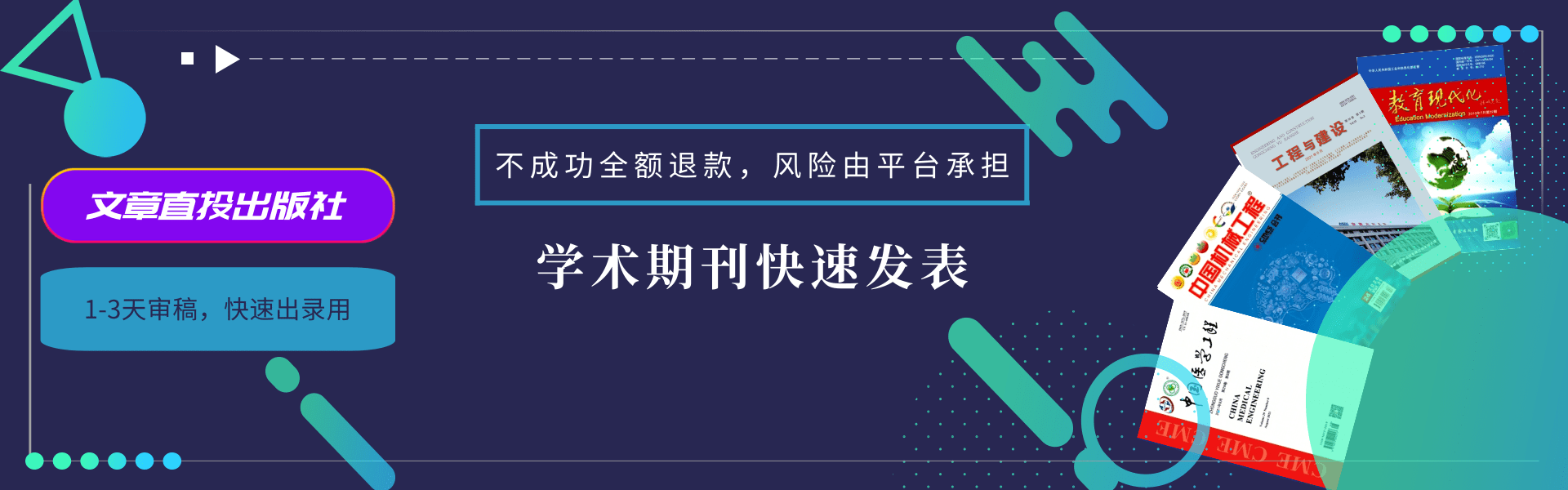郑义广
2014年第9期《语文学习》刊登韩志柏老师的《(今生今世的证据)备课札记》(下简称《韩文》),说刘亮程的这篇文章在“诗意的语言里暖昧地隐藏着潜意识中的秘密”,即用“曾经的苦难”来衬托“今天的成就”,这一次“回家”带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的炫耀,而证据的消失使这次“回家”变成了深深的遗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韩文》说,这种炫耀、自矜的潜意识“遍布全文”,而从头到尾能举出的例子却只有课文第7段这么一处:
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刷白灰时,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皮迟早会脱落得一千二净。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他们挖墙边的土,一截一截往上打墙,还喊着打夯的号子,让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打墙盖房子了。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他们也不填它,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一年又一年,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
作者认为刘亮程在此用“他们”而不是“我们”,意在说明家园废失的责任是他们的,与自己无关。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然!作者此处用代词“他们”确有深意,但绝非为了表现“超然于物外的自矜”,而是以修辞的形式竖起一道精神的屏障,表现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就像他说的:“我感到满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天边大火》)“每个人最后都是独自面对剩下的寂寞和恐惧,无论在人群中还是在荒野上。那是他一个人的。”(《远离村人》)这种孤独的情感体验贯穿于刘亮程的许多散文之中。类似课文的表述更是俯拾即是,并且无不透露出“我”与“他们”之间深深的隔膜,如:
一些年人们一窝蜂朝某个地方飞奔,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像是被遗弃。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旧慢慢悠悠,远远地走在他们前头。(《逃跑的马》)
我知道村庄周围有几块地。他们给我留下够吃一个月的面和米,留下不够炒两顿菜的小半瓶清油。给我安排活儿的人,临走时又追加了一句:别老闲着望天,看有没有剩下的活儿主动干干。(《剩下的事情》)
“我”不懂“他们”,“他们”也不懂“我”,彼此虽然并没有多少物理意义上的距离,但在精神上却又如此疏远,仿佛两个世界的人。或许有人会说,这与楚大夫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的孤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中仍潜存着某种“自矜”。这样理解看似有理,实则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简单把文中与“他们”相对待的“我”跟作者画上等号。正如刘亮程自己所坦言,其散文多是在适度虚构的基础上完成的,(笔者按:学界对散文能否虚构的问题一直有分歧,这里姑置不论。)这种虚构除了情节外,还包括人物,他说:“文学是梦学。《一个人的村庄》是一个人的无边白日梦,那个无所事事游逛在乡村的闲人,是我在梦里找到的一个人物。我塑造了一个自己,照着他的样子生活,想事情。我将他带到童年,让他从我的小时候开始,看见我的童年梦。”二是将作品与现实对号入座,文本解读过于机械,未能体察作家更深层次的思考。刘亮程在此是通过对“我”的形象塑造和情感表现,折射出每个人都会经常体验到的普遍意义上的孤独感和精神隔膜。他在接受文汇报记者周毅采访时曾说:“我并没觉得自己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只是有时候,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他们——其他所有的人是一群。我想每个人都会走到这种境地——突然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所有的欣喜与恐惧。没有谁能够帮助你,与你同享。每个人都是一个人。”
《韩文》说“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刷向灰时,‘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巴迟早会脱落得一干二净”,是一种“超然物外的自矜”。这种理解一方面在文本内外找不到有力的佐证,纯属臆想;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格调,实不可取。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泥巴和白灰的脱落绝不是因为“他们几十年前建设家同的时候就是‘敷衍”’,从文中“喊着打夯的号子”便能看出人们盖房子时的卖力。笔者生长于农村,早年家中盖房子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农村没有正规的建筑队,都是由一些会点技术、有点气力的农民组成,他们一般只活跃在几个邻近的村庄之间,农闲时才组织起来,干活的对象多是亲戚、朋友或熟人,并且干活时常会受到主人热情的款待。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干起活来会马虎了事吗?虽然刘亮程的故乡与笔者的故乡东西有别,但我想在这一点上总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那么,该怎样看待这里写到的泥巴、白灰的脱落呢?我认为,就像文中写到夕阳的消失和黑狗老死窝中一样,这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无论打夯的号子喊得多么响,墙筑得多么高,多么坚固,终有一天它们都将消逝不见。刘亮程在散文《最大的事情》中说:“风四十年吹旧一扇门上的红油漆。雨八十年冲掉墙上的一块泥皮。”“曾经从土里站起来、高出大地的这些土,终归又倒塌到泥土里。”这两句话可看作是文中这段文字的极好注脚。
刘亮程的散文十分注重表现世间万物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他会因一只搬干虫的蚂蚁而浮想联翩(《走向虫子》),会试图去揣摩一头驴的心理(《通驴性的人》),甚至会去用心地赏玩一滩极不起眼的小草(《对一朵花微笑》)。正如著名学者摩罗所说:“每一个生物或非生物比如一块石头、一棵树,他都可以同体共悲。”③刘亮程在这里便是通过泥巴和石灰的脱落,生命证据不可避免地消失,来映衬人生的短暂及时光的匆促,来告诫世人珍惜自己拥有的和曾经拥有过的一切。
另外,作者为何反复强调对发生的一切早就“知道”、早就“清楚”?这里也需略加辨析。鲁迅先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如果不对刘亮程的创作与思想有整体了解和全面把握,只拣取文中的一两个词语随意发挥,便很容易造成误解,甚至曲解。其实,作者在此并非为了炫耀自己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和预知能力,而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以及精神无处安放的焦虑与感叹。摩罗说:“刘亮程是内心早熟的作家,他对于虚无的恐惧和触摸至少从12岁那年就开始了。”这种早期产生的对于生命的焦虑意识俨然已经成为其散文的一个重要母题,像《我的死》《寒风吹彻》《一场叫刘二的风》《冯四》《一个人的村庄》《黄沙梁》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参阅,兹不赘述。
综合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刘亮程能够走进一棵草、一头驴的世界,却无法让现实中的人们心意相通,他怀着一颗悲悯的心看待世间万物,却无法将时间挽留一秒,其散文更多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及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今生今世的证据》以一种诗意、伤感的笔调描述曾经的生活场景,捕捉过往的鸿爪雪泥,透露出的也是生命的孤独感及其对人生的焦虑意识,而绝无韩文所说“富贵还乡”和“超然物外”的自矜。
(浙江省慈溪市实验高级中学 315300)